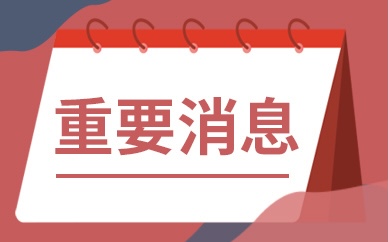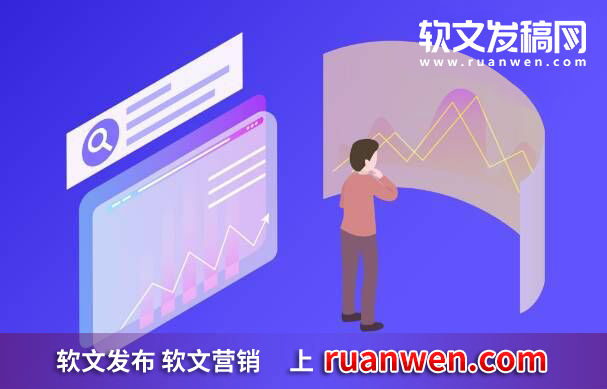□逄春阶
第二章 大有庄·老墓田
“三麻子,你怎么好下得去手!像绑猪绑狗一样,绑一个大活人?”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想起小推车,想起我父亲脚脖子上的血,四哥公冶德施忍不住又哽咽了,擦一把老泪,说:“你说,我这上了年纪,怎么泪还这么多?不见了你,我想不起来,我也不想,我就想忘记这些不愉快,这些伤心事。唉!那个场面,好多人都看见了,你说三麻子公冶令道,多么缺德啊!我给你父亲从嘴里把土粪抠出来,你父亲呕了一滩。我也骂三麻子,三麻子上来要打我,我梗着脖子说,你打死我吧,你打死我吧,被人拉开了。你父亲脚脖子上的血流了一地,我在伤口上给他摁上把干土,干土接着变成了红的,我背不动他,就扶着他回家,抹了药。后来用艾草煮水泡,折腾了一个月。这是我亲眼所见。”
三麻子公冶令道,我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,只记得他额头上一道明疤。四哥公冶德施说:“三麻子这人那么坏,咱抓着他手腕子的事儿,没有多少。没看见,就不能乱说,我就说我亲眼看见的。那是在西岭的南岩埠岭上,那时地瓜蔓子爬得不长,还没盖过地瓜沟,天有点儿热。我记得你父亲上身穿着一件背心,腰里鼓鼓囊囊,那是他的小酒葫芦,咱嬷嬷要看见他的酒葫芦,一定会夺下来,可那次咱嬷嬷没看见。我要比他们晚一个小时左右才到地里,我先到场院里去烧水,然后舀到䈰里,再担到地头。我挑着水桶,爬到西岭顶,远远地听到有人沙哑着嗓子在吼叫,我加快了步子,来到地头上,看到你父亲被反绑着,头上脸上全是浮土,三麻子用鞋底扇你父亲的嘴巴。我把担杖一扔,就过来了,问是谁绑的,三麻子说:‘我绑的,他活该!’我说:‘三叔啊,他喝上酒就不正常了,你怎么跟他计较呢!’我去给他解绳子,那绳子都肋进肉里去。三麻子不让解,说你父亲是反革命。我说他怎么反革命了?我看到你父亲的嘴巴已经肿了。三麻子对大伙说:‘他的嘴该剟不该剟?’好几个人随声附和,也有人不说话。我问,到底怎么回事,三麻子说他恶毒攻击领导。后来我才知道,什么恶毒攻击领导,是你父亲酒又喝多了,嘟嘟囔囔,骂了三麻子的爹的鬼名字‘怪够’。是啊,你父亲不该叫人家爹的鬼名字,这是侮辱人。三麻子的爹我见过,倒不是个坏人。清清气气的一个老头。他鬼名字是‘怪够’还是‘乖狗’‘怪狗’,咱也弄不明白是哪俩字。你父亲已经不正常了,怎么好绑起来打呢,还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,这帽子能随便扣吗?我把绳子解开,你父亲的胳膊已经被绑得麻木了,不能动。我一点点给他捋着,三麻子一步跨过地瓜沟,下巴颏一翘,逼着你父亲道歉,你父亲又开始说醉话,一遍一遍地唠叨。我抱住他,趴在他耳朵上说:‘十二叔,别再嘟囔了,再嘟囔小命就没了,有人想要咱的命啊!’可他控制不住。德鸿,我一直想不明白,你说三麻子怎么好下得去手!像绑猪绑狗一样,绑一个大活人?他不正常,你也不正常吗?你心怎么比石头还硬?这不是畜生都不如嘛!”
三麻子公冶令道的坟在公冶令燃的北边,紧挨着他爹“怪够”的坟,他爹活到八十五,可他不到六十岁就死了,他也死在一口酒和儿子身上。四哥说:“三麻子家在大有庄算是上等,三麻子曾经贩煤赚了点钱,可他的儿子赌博,一开始三块两块,后来越赌越大,三十五十,再后来三千两千,三万两万,把自己的小家赌光,老婆跟着人家跑了,三麻子的家底也全部赌上。三麻子走投无路,去找了藐姑爷给掐算,藐姑爷给他出了个主意,得请出他爹‘怪够’来管。怎么请?抱着儿子穿的衣服,到他爹的坟上,求他爹出来管孙子,绕着坟正转三圈,倒转三圈,再给爹发个喜钱。抱着衣服来回都不能跟人说话,一说话,衣服上的训词就冲了。哄着儿子把衣服穿上就好了。三麻子如此这般照着藐姑爷说的做了,也不管用,儿子照赌不误,这败家子管不住自己的手了。三麻子公冶令道天天借酒消愁,有一天夜里,跟几个发小喝酒,发小怕他喝醉,不敢劝,可他抢着喝,任谁也摁不住,喝了一个时辰,扶着墙上茅厕,一头砌到尿池里。等发现时,已经晚了。”
三麻子的坟上盖着一丛枯草,我盯着这坟。就听四哥说:“三麻子啊!你不是厉害吗?你出来啊!你再绑俺啊,你再扇俺啊!你出来啊!”
在公冶令燃的坟边上,还有一座新坟。四哥说,那是公冶令斓姑姑的。
我一直觉得,令斓姑姑是大有庄最漂亮的女人,她年纪不大啊,也去世了?
我忽然想起五十年前的那个雨天。
壹点号老逄家自留地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
关键词: